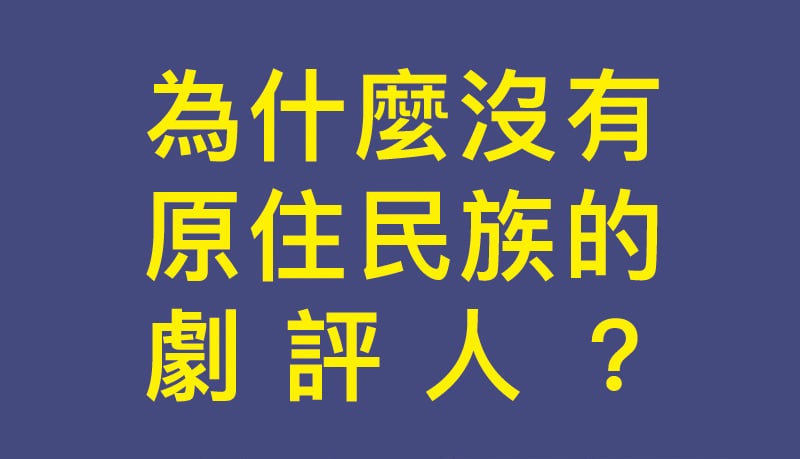
文:盧宏文
(2017年入會,現任理事。隨緣寫評,現居花蓮)
搬到花蓮後,開始有機會接觸到原住民族的創作者,雖然未必每一場看過的演出都會寫評論,事實上是寫得很憊懶,但只要有時間,我盡可能不露掉任何一場。觀賞原住民族創作者的作品,總是充滿著許多感觸與謎團,而只有感觸是很難寫出評論的,破解謎團成為一項重要的功課,無論是觀演前,或觀演後。我知道有些人對於評論的想法是,在觀看前盡量不做任何功課,但醒醒吧,或承認吧,我們跟Pina Bausch的距離,或許比跟Watan Tusi的心靈距離還近些。 為此,以漢族身分書寫原住民族的劇評,總令人充滿遺憾,或帶著一點罪惡感,對眼前的文化脈絡如此無知的我,如何書寫評論呢?這個想法至今仍伴隨著我,但有一個新的疑惑亦從此產生,如果我這樣的書寫是一種昭示與自我揭露,那麼對應於此的內部觀點、基進觀點,或是以原住民族身分為主體的觀點, 為何不見蹤影? 這樣的觀點非基於本質論的血緣上,而是以政治光譜上的身分認同作為劃分。去年《PAR表演藝術》7月號的「續聊天」專欄,周伶芝、郭亮廷邀請了TAI身體劇場的瓦旦、以新談近期觀看的作品,後者批判的角度犀利,但要不是前者積極助攻,恐怕我們又將缺少一次聽到內部觀點的時機。就內政部109年底的統計,原住民族約佔全國人口的2.45%(實際上把未獲認定的族群算進去,應該更多),那麼,何時會等到一位原住民族劇評人的現身呢?
原文連結: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1HWwj7rjzz/
________________
「評論的問題意識」編註
於會員召募「倒數計時」期間,敝會逐日刊登由五位會內的劇評人,就「評論的問題意識」撰寫之短文,每一位提出一個問題,並簡要闡述。評論面向公眾,先於自我宣傳。(邀稿:吳思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