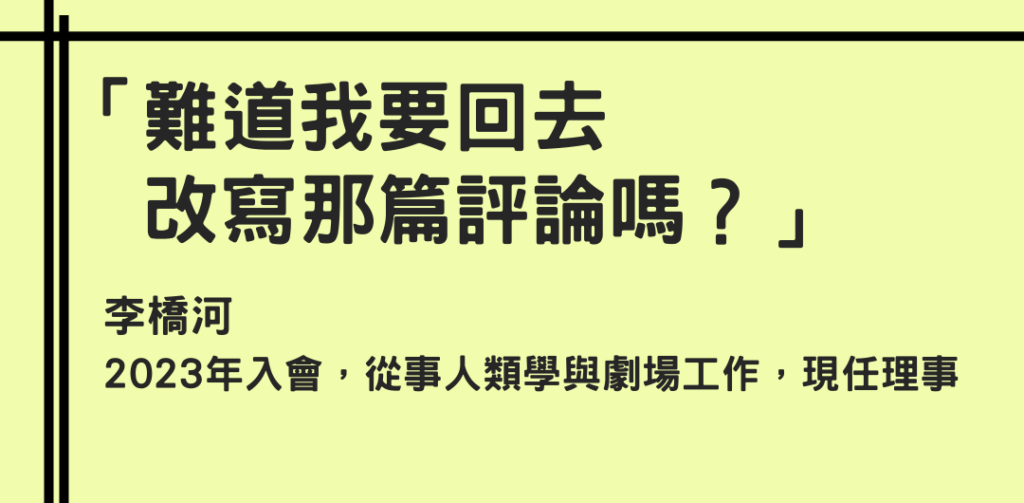
文:李橋河
(2023年入會,從事人類學與劇場工作,現任理事)
曾經,一位評論人這麼問我。過去寫過正面評價的創作者在近年被人指控妨害性自主的惡行,使得這位評論人也重新反思自己是不是在無意間成為捧出體制怪獸的幫凶。回應這個問題,我認為改寫評論的效益恐怕並不如想像中理想:一方面,回溯當時對作品的感受並不容易;另一方面,用後見之明重新行文也很難找到能夠讓自己信服、讀者滿意的說法。
那麼,評論人可以怎麼面對自己與藝術生產機制的關係呢?有些評論人選擇聯繫曾經發表評論的平台,簡要說明該位藝術家何時被揭露妨害性自主的罪行。
透過註解與附註,評論人並不是要對個案進行道德審判,而是在區分藝術作品的價值與藝術家的行為時,也並置作品背後多重訊息的複雜性。這樣的做法不是要粗暴地在「取消」或「保留」的兩極上選邊,也不是在簡化「道德」和「美學」似是而非的對立——相對地,它的目的在於要求補充讀者必要的背景資訊,使觀眾能夠更全面地參與進藝術價值與道德責任之間的協商過程。
在這裡,讓我們回到要不要改寫評論的問題:與表演藝術的轉瞬即逝不同,評論文字往往是對於作品第一手紀錄的留存;然而,與其將既成的評論文字視為囿困觀點或定著關係的枷鎖,或許我們還可以將它們看作供給跨時代眾人圍繞作品、持續遭逢的基底和平台。
創作本身作為一場社會溝通的實踐,評論則是基於上述廣大過程中延伸續航出的部分旅程。正是因為有評論文字,使人們可以展開各自的方式接繼加入賦予意義、對位脈絡的動態過程;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過程,使我們更能夠從中協作出一條條思考藝術、回應社會的參與路徑。
原文連結: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12JgZ1m13kU/
「對評論的提問」編註
於會員召募「倒數計時」期間,敝會刊登由四位會內的評論人撰寫之「對評論的提問」。本計畫承襲自2022年會員招募期間「評論的問題意識」,借用彼時編者吳思鋒之語:評論面向公眾,先於自我宣傳。(邀稿:余岱融)